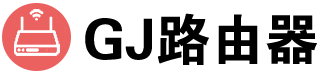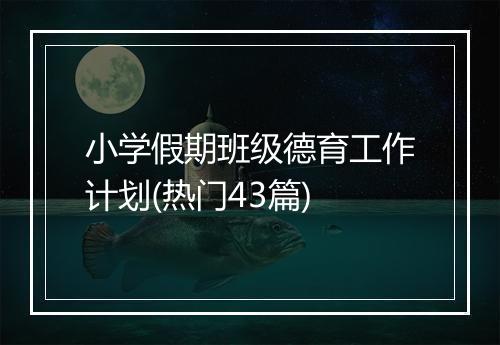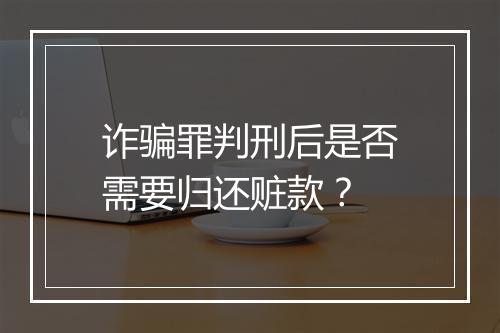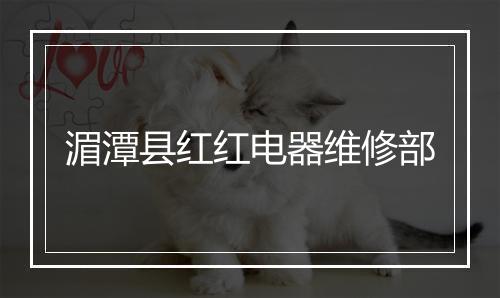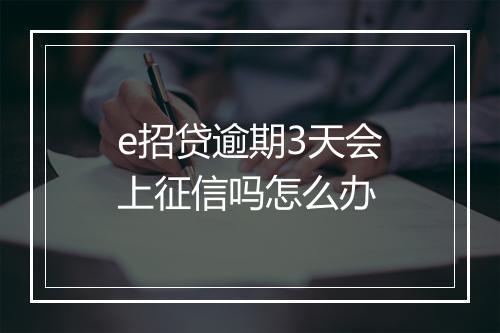前言:
当前咱们对“双性鲤鱼乡”大约比较注重,同学们都需要剖析一些“双性鲤鱼乡”的相关资讯。那么小编也在网摘上收集了一些有关“双性鲤鱼乡””的相关资讯,希望各位老铁们能喜欢,咱们快快来学习一下吧!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是经历这种动荡和剧变的最深度体验者,她们在文学中就不可能保持某一类固定形象不变,她们对哲学、宗教和政治等的观念都会有不同的审美体验,她们所要展现的是一种多元化的、未被某种理论或秩序所限制的思想形态。
“在英国的前现代主义时期,妇女写作进入公共领域面临着两大压力:一是宗教,二是政治。清教文化鼓励妇女在公共场像牧师那样所讲述她们的宗教经验,出版与宗教相关的赞美诗和散文,把自己的信仰体验和转变用自传的形式写出来。”
“18世纪以后,英国妇女的生存条件较之前代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妇女均有了较大的改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上升和海外殖民地的开拓,英国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了。以前,许多妇女不得不在操持家务的同时,还要从事小规模的家庭作坊经营。随着机械化生产规模的扩大,她们已不再被要求从事生产劳动。但由于其在夫权文化中的边缘地位,公共的经济、政治事务仍然将之排斥在外。于是,有着充裕闲暇的妇女就将博览群书作为主要的消遣。而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与广大妇女成为小说市场消费主体的同时,一部分富有才情的妇女也逐渐向创作主体转变。她们逐渐从被动阅读与接受,发展为主动提起笔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尤其对婚姻不幸的妇女,写作也成为摆脱经济依附,寻求自我实观的现实工具。”
在18世纪以后,除了文学史上提到的著名作家,如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Gaskell)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外,还有一大批活跃在新教背景下的妇女布道者,她们通过传道不仅参与了公众生活,而且还撰写了大量的布道书、回忆录和富有政论性质的小册子。
“她们要求并且获得了评论政府、军队、法律机构、医疗行业和商业等公正与否的权利,并以最高权力的上帝名义谴责那些不公现象。”这种宗教教育氛围客观上促使妇女学习语言,尝试诗歌体和自传体写作,并且能够让她们离开家庭生活的小圈子进入社会公众生活。因此,英国知识女性从中世纪始就意识到知识和受教育对于自身成长和参与社会现实的重要性,知识女性也从那时起作为一种常见文学形象见诸各类文学形式中。
有一则故事《弗拉芒卡》如此叙述:
“女人如果能稍学一点东西,那完全会变得更好。小姐,请你告诉我,如果你不是像你这样什么都懂,那么,你会怎样度过这两年的光阴呢?你会怎样忍受如此残酷的折磨呢?你肯定会死于过度的忧郁。但是,无论你遭受乐多大的痛苦,只要你读一些东西,痛苦就会烟消云散了。”
知识女性从关注自我到参与社会生活,并期望影响传统的女性观和价值观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直到《为女权辩护》的诞生,那种顾影自怜或自我疗养的方式才得以改观,并逐步转向去挣脱束缚在女性身上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枷锁。历史、现实和文学中的知识女性作为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铸就了一份宝贵的英国文学遗产。文学与现实与历史从来都不可能截然对立和分开,它们的复杂关系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摹仿论所能概括的。
在描述知识女性思想的变化轨迹时,不得不冒着把它们论述成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定论性质的思想的危险。知识女性的生活和思想其实只是一些情感和态度,一些观点和主张,她们的存在是整个人类生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使得人们不会因为某种单一思想而迷失在自我认同的陷阱中。与维多利亚时代相比,英国20世纪知识女性的客观存在是整个知识生活氛围的重要保证,她们也为英国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
20世纪初,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三类“妇女与小说”的关系:
“妇女与小说这个题目可能意味妇女以及她们像什么样子,这也可能是你们出这个题目的本意;也可能意味着妇女和她们所写的小说;也可能意味妇女以及描写她们的小说;也可能意味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上述三者错综复杂地混在了一起……我应该永远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描写她们的小说”的一小部分人无疑是知识女性。考虑伍尔夫演讲的地点,她所面对的听众,以及英国当时的社会氛围,她不得不使用迂回曲折的话语技巧:“谎言将会从我的嘴唇里流淌出来,但是也许有某些真实与这些谎言混淆在一起,须由你们把这真实找出来,并且判定它的任一部分是否有保留价值;如果没有,你们当然就会把它整个儿扔进废纸篓里,并且把它完全忘却。”
现在我们不用再使用如此谦逊而充满修辞的语言,而是要把文学作品中知识女性形象的思想轨迹和审美过程挖掘出来。知识女性从阶级属性来说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她们具备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受过教育;具有思想;参与社会生活。其中“思想”是最重要的,它是在物质财富之外保持一个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最基本要素。
生于1919年的多丽丝·莱辛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对“思想变化”的情有独钟:“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思想是如何变化的,我们认识现实的方式是如何变化的。”因此,我们要关注的是知识女性的思想变化的叙述形态,而不仅是某种形象的归类,但是这些思想又是归属某种叙述形态的;不是人们认为她们在当时所具有的思想,或是她们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而是半无意识地或者被批评者忽略的那些指导她们行动的那些思想,她们赖以生活和写作的思想。
这类思想“不管它是多么微小,它却有着独特的神秘性质——如果把它放回到脑海之中,它就立即变得使人非常激动,并且重要;而当它猛冲并下沉,而且四处闪光之时,它又形成了思想的一种极大的汹涌和波动,结果若想平静地坐着则是断无可能。”
这种思想是比形象本身更为广阔和敏锐的东西,“思想的小鱼”只有在安宁的精神和环境中才能自由地游玩,如果遭遇外部刺激和打扰,就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被吓跑或吓傻,躲进岩缝中再也不出来;二是被刺激得更欢,大有鲤鱼跳龙门的意气风发;三是被同化,对外界的影响不闻不问。
这些“思想的小鱼”其实就是知识女性对于自己作为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和完整性的把握,它们是女性意识的一部分,但它们往往又不能简单地用“女性意识”来概括。S·J·卡普兰(Sydney Janet Kaplan)在《当代英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中对于这种特殊的包含“思想”的“女性意识”如下概括:
“当我用‘女性意识’这个术语时,我希望读者知道我是以相当特殊和狭窄的方式运用它。它不是指妇女对自己的女性气质的一般态度,也不是妇女作家群中某种特有的情感。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文学手法:是小说写作中刻画妇女的一种方法……我用‘女性意识’一词甚至不是泛指一部小说中某一妇女意识的整个涵盖面,二是指她的意识中把她自己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存在加以界定的那些方面。”
因此“思想”既与总的社会、经济形势相联系,又因为女性的特殊存在而与众不同,尤其是在小说中表现出来,其意义自不一般。社会文化形势产生相应的小说形式,而文学思潮又对形成某种形势产生影响,或者说,这些文学思潮或派别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形势,它们对于知识女性的生存和写作产生着巨大影响。
知识女性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她们有家庭、有友谊和关注她们的人群;在变动的时代中,在以男性理性和自由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她们更能深刻而敏感地体验到作为知识分子和作为女性的作用和身份。
因此,20世纪英国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形象及其所附着形势内涵具有更多的意义:它将使人们想起启蒙理性以来所确立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某些变化,想起英国知识女性在参与形势变化过程中的种种故事,看到知识女性在传统、宗教、战争、政治、爱情和婚姻家庭中的所思所行,以及她们如何运用各种叙述形态对上述内容进行审美把握的。
在20世纪之前,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基本上可以分为失去固有形状的两类形象:一类是天使,如《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和《浮士德》中的玛甘泪;一类是疯女人,如笛福笔下的摩尔·弗兰德斯、狄更斯的得伐石夫人、理查森的克拉丽莎和萨克雷的阿米利亚等的描写。她们往往成为男作家表达某个主题和思想的装饰,或是为了衬托男主人公的伟大。
但是,我们也看到19世纪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充满优越感:她们或以平等自由的人格影响男主人公,如《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和《简·爱》的女主人公;她们或凭借高尚的道德精神充当男主人公的精神向导,如《劝导》中的安·艾略特和《呼啸山庄》的小凯瑟琳等;她们或因为自我批评和反思的态度赢得高大的自我形象,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亚·布鲁克和《爱玛》的女主人公。
所以有人指出这种充满吊诡意味的文学现象:“在最终意义上,妇女比男人优秀是活跃在19世纪女小说家女性意识机制中的基本因素。”无论是执着于爱情,还是在男性面前自我反思,这些女性形象似乎都有着精神分析学家所谓的“自恋癖”:“女人由于缺乏认同感,不自觉地趋向内向,把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将自我客体化,将自己变成男性关注的目标。”当自我关注的空间和想象变得越来越集中时,就会产生自明式的女性形象,或走向纯粹的私人化写作。由“自我关注”到“他者关注”,其间是一种客体化过程,而不是一种主体性的审美化过程,这也势必造成更大的差距。
这种充满差距的、潜意识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成规是否本身就表明了整个19世纪时代环境的氛围——妇女自我意识和道德意识的浮出地表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落实。因此,妇女作家便通过这样一种虚构的方式构筑理想的生活蓝图?男作家与女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位于南北两极,一贬一褒,他们(她们)的书写是否尊重两性间的真诚差别?毫无疑问,这两类描写都显得有些过度或夸大,都似乎缺乏真实的自然的品格。
到了20世纪,伍尔夫特别预见了两类描写方式的正常状态,对于男作家的合理创作状态,伍尔夫如此描述:
“倘若他是冷静地写着女人,用无可争辩的论据来确立他的论证,并且并无迹象表明他希望结果是此而非彼,那么我也就不会愤怒。我就会承认事实,就像承认豌豆是绿的、金丝雀是黄的这个事实一样。”
对于女作家的合理创作状态,伍尔夫如下表述:
“如果有人想总结当前妇女小说的特征,他/她会说它是勇敢的,真诚的,与妇女们的所感所知密切关联的。它并非怨恨十足。它并不一味强调自己的女性特质。”
从伍尔夫的论述可以看出,为了说明或突出某个问题或某种事实,任意扩大两性区别的文学描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女性形象的整体性、完满性和审美性。
男作家和女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都是值得关注的,知识女性并不是女作家书写的专利,知识女性也不只是作为女作家表达女权意识的出口。因此,如果仅仅对女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作性别差异、女性主体、女性传统和后女性主义等女性批评,势必影响甚至削弱知识女性作为社会个体、文化成员和审美主体等人类意识中共通的东西,形成一种“分离主义”批评。
“男女的世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绝对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男作家也可以在其文学创作中对这一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审美性的人物形象进行描摹。当然,这其中具有显著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除了因为作家的性别不同所导致的外,我们更应该从其他方面来寻找这种书写方式的不同,文学传统、个体特色、时代现实和历史发展等因素都是我们应该考虑进去的。
正如德国学者倍倍尔的论断:“除了自然为了达到自然目的所设置的两个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别之外,一切差别都是不合理的。”基于挖掘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的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批评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片面性,西方有学者指出“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这样过分强调作家的性别,不可避免地对作家社会身份的其他方面进行限制或压制。”
因此,对于具有男性和女性的双性视角批评显得尤为重要,“仅仅书写男人绝不是在书写普遍的文学”,同样,仅仅书写女人也绝不是在书写普遍的文学。文学中的知识女性形象被男作家或女作家书写,无论其中有着怎样的“性政治”和各种各样的“傲慢与偏见”,更何况,这些看似不公正的现象很多时候是研究者的预设,并不是每一部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书写都带着性别歧视的信息,他们都是在父权制文学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创作也必然体现出一种“双声话语”现象。
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代妇女作家都发现她们没有历史,她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过去,一次又一次地锻造她们的性别意识。”因此她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把妇女文学分为女子气阶段、女性主义阶段和女性化阶段。从她分析和划分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对“性别意识”尤为看重,这是一个旨在强调与主流文化文学有差别的女性文化、女性传统和女性文学的研究时期,并且还蒙上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色彩,因此也就多少忽略了社会、历史、传统之外的“女性想象力”和布鲁姆所谓的“审美体验”。
知识女性已经从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知道如何避免陷入“疯女人”和“家庭天使”的生存状态,知道激进女权主义所带来的种种束缚,知识女性既不是家庭天使,也不是权力附庸,知识女性在社会习俗、历史意识和现实经验之外看到了更多的自由的、充满艺术想象的事物,并不断“接受一种不同于自身本质的存在”,由此获得了诗学意义上的“思维”:女人是天生的,女人也可以不变成女人。
这种思维肯定了生理学意义上的女人,更在于突破社会常规意义上对女人的界定——女人是变成的和规训的,但是女人也可以不变成这种女人。随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知识女性不是处在一个稳固的男女二元社会结构中,其生存环境是多元的、复杂的和不固定的,“透过复杂性,在相互关联中看事物,意味着从依赖现实的线性和专制的概念及思想两分法的逻辑与话语领域中走出来。”这种复杂性和关联性的研究也正是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所表明的,男人说中的女性形象也应该放在相互间的关系中来刻画,因此,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也必然反映这种多元性和流动性。
别林斯基于1842年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与审美的”文艺批评观:
“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每一部艺术作品一定要在对时代、对历史的现代性的关系中,在艺术家对社会的关系中,得到考察;对他的生活、性格以及其它等等的考察也常常可以用来解释他的作品。”
别林斯基认为审美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相结合才不会导致片面,但是在具体文学批评中,结合具体的文学文本,不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必须有所侧重,有所取舍,这也符合作家创作的个性以及他们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对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取舍程度。
“妇女还应该在思想领域与男子竞争;她们不能等着男子们在他们愿意的时候为她们开发大脑潜能,替她们开辟道路。”同时,对于“文学中女性角色和女性意识的狭隘表现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因此,在探索20世纪英国小说中知识女性形象所具有审美内涵时,要避免陷入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或女性主义批评中,而不能得出关于知识女性形象的整体内涵。
对于当下的创作者而言,无论是男性创作还是女性创作,完整女性形象的塑造要努力达到诗学意义上的效果:女人是天生的,女人也可以不变成女人。那么,塑造知识女性形象无疑是人们的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