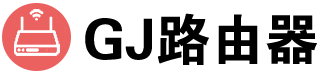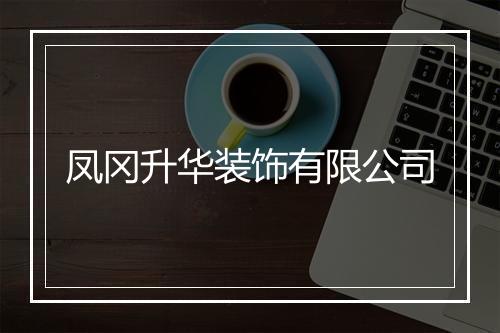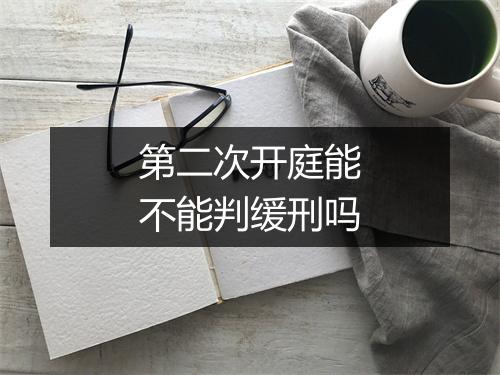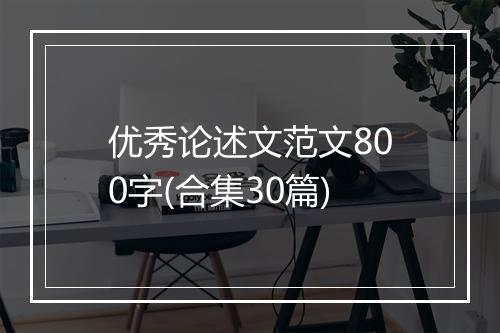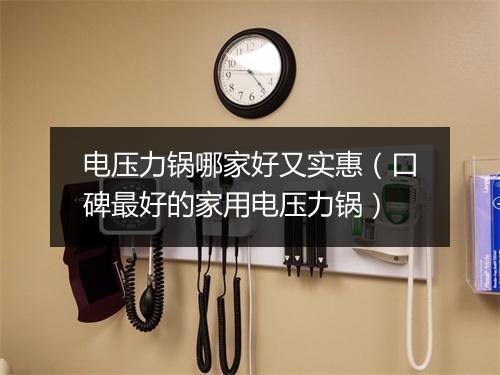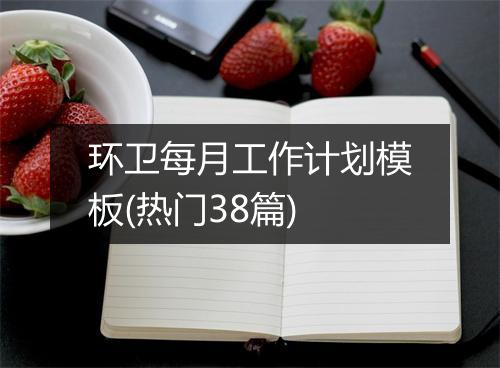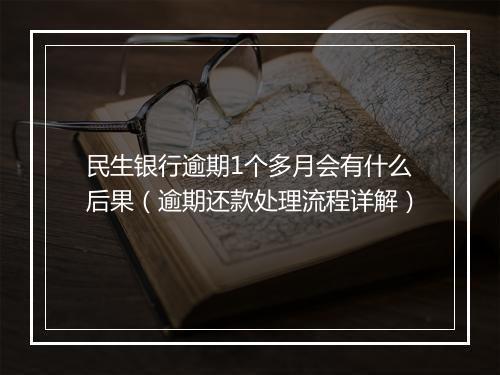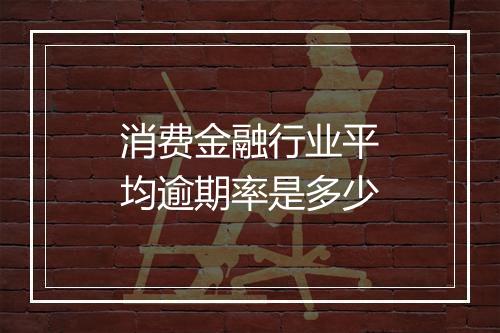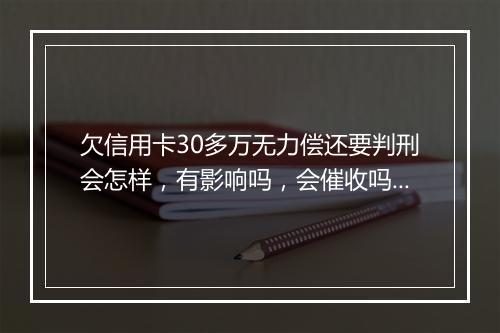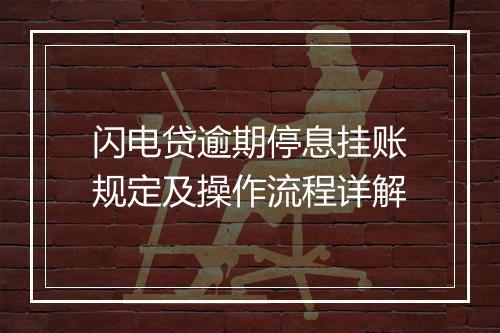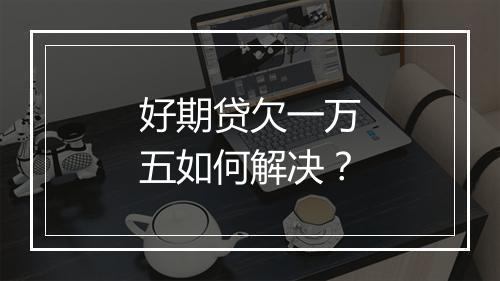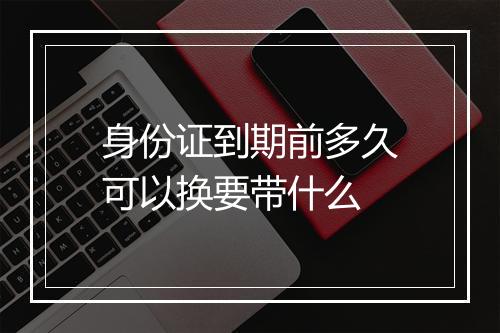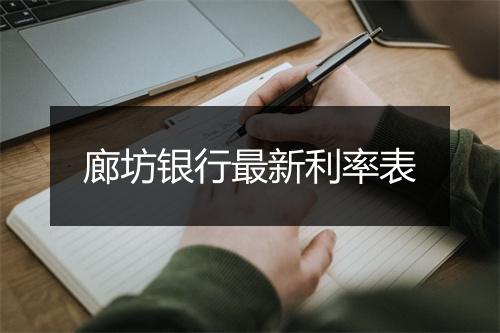本文内容从各个方面解释了不同的讲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小编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签订担保协议被认定无效后,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吧。
(2020)最高法民终881号
【裁判要旨】
担保协议因签约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无效,故其对担保协议的无效并不具有过错。原《担保法解释》第7条并未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无过错的情形。即使认为该条文涵盖了该情形,亦仅是针对担保人责任的一般规定。
而原《民法总则》、现《民法典》第22条是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利益的特别规定,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应适用《担保法解释》第7条的一般规定。根据当时有效的《合同法》第58条及《担保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时的赔偿责任系缔约过失赔偿责任,赔偿须以过错为前提,如担保人对担保合同无效无过错的,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
本案系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李春平在签署案涉协议时是否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春平于2016年6月签署案涉系列担保协议系为借款金额为2.5亿元的巨额借款提供担保,属于特别重大复杂的民事行为,并非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普通民事行为,故本案必须确定李春平在签署案涉协议时是否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
首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民事判决,宣告李春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该判决所依据的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于2017年5月11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李春平患阿尔茨海默症具体起病时间不详,但至少从2016年8月1日起至今受轻度智能缺损影响,对事物认知的能力受损,故《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上述鉴定结论与北京安定医院的诊断结论是一致的。中诚信托公司主张李春平至少自2016年8月1日起有“认知损害”,但没有达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程度,与《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相左,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李春平于2016年6月签署协议时处于轻度智能障碍状态,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系综合本案全部证据以及阿尔茨海默症病情发展缓慢而稳固的特点、一般生活常识以及社会经验所作出的合理推定。
此外,从李春平的就医情况看,其自2016年3月起由家人陪同先后去过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安定医院等就诊。其中,2016年3月3日中日友好医院的检查结果记载于《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该证据的证明力应予以确认。中日友好医院的影像检查结果为李春平存在腔隙性脑梗塞、轻度脑白质变性、脑萎缩情况,而从《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内容看,腔隙性脑梗塞、轻度脑白质变性、脑萎缩说明患者存在脑器质性病变及智能缺损;2016年7月22日北京安定医院初步诊断结果为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老年前期型),上述证据与《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够相互印证。
由于阿尔茨海默症具有起病隐匿、持续性且不可逆的智能衰退等特点,一审法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李春平至少从2016年8月1日起有认知损害的鉴定结论,推定李春平于2016年6月前后已经处于轻度智能障碍状态,有充分证据证明,并无不当。中诚信托公司主张《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于2017年5月11日故仅能证明从该时间点起李春平进入轻度智能障碍状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三,中诚信托公司不能提供有效的反驳证据证明李春平于2016年6月签署协议时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中诚信托公司提供的公证书系对李春平的签字真实性和委托意愿进行公证,而非对李春平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公证,故公证书尚不足以证明李春平与2016年6月签署系列担保协议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从李春平参加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8884号案庭审的视频录像看,并未显示出李春平清晰流利地回答法庭提问。相反,李春平庭审中言语欠流利,赘述性用语表现明显,答非所问,举止行为已经表现有异于常人,亦再次印证阿尔茨海默症发病具有隐匿性、持续性且不可逆的智能衰退特点。李春平参与该庭审的视频录像不足以证明李春平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一审法院认为中诚信托公司仅提供林杰、中科联合公司单独拍摄李春平签署案涉协议的视频而不能提供其他担保人签署案涉协议的视频,有故意为之之嫌,这在表述上虽有欠妥之处,但该视频证据反映了李春平签署巨额担保协议时被动服从林杰在旁指点等有异于常人的精神状态。
中诚信托公司还主张《借款合同》项下的1亿余元由道行天下公司支付至李春平指定的北京奔月华程商贸有限公司账户,由李春平使用,但并未举证证明李春平实际控制北京奔月华程商贸有限公司或李春平使用了上述款项。
综上,中诚信托公司提供的反证不足以证明李春平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关于第二争议焦点其应否承担连带保证及抵押责任或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民法上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充分考虑了保护欠缺行为能力人的利益和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两种法益之间的平衡。意思自治是贯穿民法始终的价值理念,只有行为人对其行为性质及后果具有识别能力,行为人才能对其行为承担责任。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二条做了相同的规定。
即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制度构造上优先保护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仅在法定情形下例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从事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或从事的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态不相适应之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等情形,才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这一制度为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免遭损害筑起安全保障之堤,体现了同情、关爱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弱者权益这一人类的基本情感。
首先,由于李春平于2016年6月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认知能力受到损害,对担保2.5亿元本金及利息之巨额债务这一重大复杂的民事行为并无相应的认知能力,其从事的签署案涉担保协议的民事行为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且法定代理人拒绝追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李春平上述担保行为无效。相应地,林杰实际控制的中科联合公司将其所管理的李春平房产,基于李春平签署的《房地产抵押合同》而办理抵押登记的行为也归于无效。一审法院根据当时有效的《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以及《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认定李春平签署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不可撤销)》、《房地产抵押合同》及《承诺函》均为无效,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中诚信托公司上诉主张根据当时有效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对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由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然而,案涉担保协议因签约人李春平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无效,故李春平对担保协议的无效并不具有过错。上述第七条并未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无过错的情形。退一步说,即使认为上述第七条涵盖了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无过错的情形,该条亦仅是针对担保人责任的一般规定。
而原《民法总则》、现《民法典》第二十二条是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利益的特别规定,强调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其从事的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之民事法律行为不承担责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除外。
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应适用当时有效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一般规定。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时“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时的赔偿责任系缔约过失赔偿责任,赔偿须以过错为前提,如担保人对担保合同无效无过错的,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签订担保协议被认定无效后,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看法,文章内容就讲解到这里了,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那就请寻找专业律师为您解答吧!